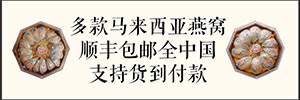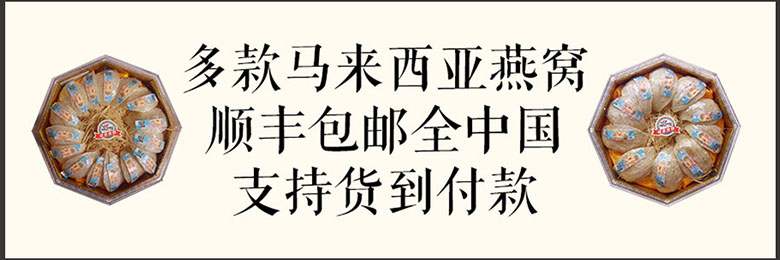小曹無意中看到第十經(jīng)濟(jì)觀察室的文章,說到關(guān)于馬來西亞的前世今生,覺得相當(dāng)中肯和全面,于是就轉(zhuǎn)發(fā)到了自己的博客上來,希望對(duì)想要了解馬來西亞的各位有用。

舊夢(mèng):中世紀(jì)第一世界的強(qiáng)國記憶
每一位馬來人都有一個(gè)巨港強(qiáng)國的回憶:三佛齊和馬六甲王朝曾經(jīng)的三分天下(充當(dāng)海上絲綢的貿(mào)易中轉(zhuǎn)點(diǎn)),稱雄東南亞諸國,構(gòu)成了馬來人身份認(rèn)同的最直接來源。
在公元7世紀(jì)-14世紀(jì)(大約相當(dāng)于中國唐朝到明朝初年的歷史),三佛齊占據(jù)了今馬來西亞的大部,印度尼西亞的西部,首都設(shè)在巨港城;三佛齊人民風(fēng)彪悍,善于水戰(zhàn),他們?yōu)閺V州的阿拉伯商人運(yùn)貨回中東提供補(bǔ)給中轉(zhuǎn)站,也為印度商人來東南亞貿(mào)易提供武力保護(hù),以此獲得了巨量的國際貿(mào)易利潤(rùn),因而國力強(qiáng)盛,稱霸一時(shí)。
盡管三佛齊的很多國王接受了中國皇帝的冊(cè)封,也履行了朝貢的義務(wù),但三佛齊人仍然認(rèn)為自己是獨(dú)立于阿拉伯與中國之間的第三方勢(shì)力,他們甚至鼓勵(lì)本土學(xué)者,尋找以及創(chuàng)造自己文化的獨(dú)特性、優(yōu)越性。
如果說中世紀(jì)(5世紀(jì)-15世紀(jì))有第一世界的話,三佛齊人認(rèn)為自己和華夏、阿拉伯屬于第一世界,歐洲、非洲以及東南亞諸國屬于第二世界、第三世界。
三佛齊滅亡后,馬六甲王朝繼承了衣缽,但馬來人的信仰卻從佛教逐漸轉(zhuǎn)移到了伊斯蘭。
馬六甲國王從永樂皇帝的冊(cè)封中獲得了法統(tǒng),從鄭和主導(dǎo)的西洋貿(mào)易中,得到了充分的好處,馬六甲得以重新統(tǒng)治馬來半島,但歷史很快進(jìn)入15世紀(jì),葡萄牙、荷蘭以及英國先后到來,馬六甲王朝分裂為數(shù)百個(gè)的大小邦國,馬來半島也逐漸淪為半殖民地、殖民地。
在葡萄牙、荷蘭以及英國的爭(zhēng)斗中,英格蘭人最后獲勝,1874年,英國通過《邦咯條約》,將馬來西亞各邦變成自己的保護(hù)國,然后以海峽殖民地(新加坡)為前進(jìn)據(jù)點(diǎn),通過軍事威脅、經(jīng)濟(jì)利誘、民族挑撥(華夏人、印度人和馬來人的爭(zhēng)斗)等高超的統(tǒng)御技巧,又將馬來各邦國變成直屬管轄殖民地。
盡管英國殖民壓迫異常殘酷,但客觀上也為馬來半島的統(tǒng)一提供了最好的溫床。早在三佛齊王朝分崩離析后,馬來半島就分裂為數(shù)百個(gè)大邦國、小貴族領(lǐng)主(馬六甲王朝只實(shí)現(xiàn)了部分統(tǒng)一),隔離500年,都宣稱擁有獨(dú)特的文明。在經(jīng)濟(jì)和政治、文化層面,隸屬于不同的大國:如馬來北部的吉打邦、吉蘭丹邦以及丁加奴邦,是暹羅泰國的勢(shì)力范圍;西部海岸的馬六甲州、雪蘭州與蘇門答臘島(今屬印尼)東海岸的人種更為接近,
三佛齊和馬六甲王朝都是以貿(mào)易立國,馬來人因財(cái)而聚,并沒有形成很強(qiáng)的向心力文化,隔離數(shù)百年,獨(dú)立情緒更盛。英國殖民者通過暴力手段,把這些獨(dú)立邦國完成了行政隸屬的統(tǒng)一;同時(shí)在馬來半島建造鐵路、海港,以方便為歐洲提供錫礦、橡膠、木材等原材料,客觀上讓馬來半島完成了市場(chǎng)的統(tǒng)一;而英國特別是日本殖民馬來半島期間,通過刻意排斥華夏人和印度人,制造民族矛盾,強(qiáng)化穆斯林信仰+本土生的馬來主人地位,形成了馬來人民族認(rèn)同的統(tǒng)一。
行政隸屬、市場(chǎng)、民族認(rèn)同三統(tǒng)一,量變引發(fā)質(zhì)變,喚起了馬來人,國家獨(dú)立和民族獨(dú)立的思潮。
裂變:馬來西亞的新文化運(yùn)動(dòng)
國家獨(dú)立和民族獨(dú)立的思潮萌芽后,首先第一個(gè)問題就出現(xiàn)在馬來人眼前:為什么馬來人落后了,為什么馬來人先后被葡萄牙、荷蘭、英國殖民?
或許是受到中國新文化運(yùn)動(dòng)的啟發(fā),馬來西亞的穆斯林精英也開始討論一些觸及靈魂的問題:為什么馬來人沒有“塔瑪敦”(tamadun)。這是一個(gè)新造的詞語,用以指技術(shù)文明,與中國文化精英反思儒家文明為什么沒有誕生科學(xué)和民主一樣。
在當(dāng)時(shí)的一個(gè)表達(dá)現(xiàn)代主義伊斯蘭雜志《伊瑪目》上,穆斯林精英沉痛的說:馬來人被白種人征服了,我們要行動(dòng)起來,團(tuán)結(jié)起來,‘反帝,反‘封建’;通過加強(qiáng)傳授下一代西方技術(shù),實(shí)現(xiàn)馬來西亞的獨(dú)立和富強(qiáng)。
但是,由于近代的馬來半島上,華夏人、印度人和馬來人三分鼎立,華夏人一度超過了一半人口,占據(jù)著城市中心、控制了馬來半島上大部分的商業(yè)和礦產(chǎn)資源;穆斯林精英擔(dān)心對(duì)傳統(tǒng)[全面否定],[全面西化],將使得馬來人失去團(tuán)結(jié)的紐帶,在與華夏人競(jìng)爭(zhēng)中,被驅(qū)趕出馬來半島。
在馬來亞人薩赫恩.艾哈邁德撰寫的一部影響力很大的小說《部長(zhǎng)》中,虛構(gòu)了一個(gè)未來:華人掌控國家,馬來人被驅(qū)趕到叢林。《部長(zhǎng)》暴露了馬來人對(duì)華夏人深深的恐懼,是馬來版本的《黃禍論》。
所以,為了對(duì)抗印度人和華夏人,穆斯林一些開化精英和青年才俊對(duì)傳統(tǒng)與宗教的落后面批判淺嘗輒止,不夠深入,現(xiàn)代化、世俗化的理念僅停留在精英上層,并沒有深入馬來民眾的人心,效果非常有限,這對(duì)此后馬來西亞進(jìn)行現(xiàn)代化、工業(yè)化,起到了非常強(qiáng)大的拉阻效應(yīng)。
重生:馬來官、華夏商、印度農(nóng)的混血馬來
1957年,馬來西亞取得了獨(dú)立,但直到1970年之前,馬來西亞的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重心是在消除華夏人、印度人和馬來人之間的經(jīng)濟(jì)差距,更直白的說:通過政治博弈,從華夏人、印度人手中,爭(zhēng)奪更多經(jīng)濟(jì)權(quán)力。
由于歷史的原因,在英國殖民以及其后的日占時(shí)代,馬來西亞形成了殖民者和馬來人掌握官僚系統(tǒng),華夏人控制商業(yè)和采礦業(yè),印度人喜好種植園的格局,也就是說,馬來半島的經(jīng)濟(jì)大半被華夏人占據(jù),城市中心居民也主要是華夏人,獨(dú)立后的馬來人想要改變這種狀況。
所以,除了接收英國和日本的殖民產(chǎn)業(yè)外,獨(dú)立政府再次強(qiáng)化了馬來人在政治、經(jīng)濟(jì)、教育方面的特權(quán)。
代表華夏人和印度人權(quán)益的政黨馬華公會(huì)以及馬來印度國大黨,[竟然]承認(rèn)了馬來人作為“大地的子女”的主人地位,接受馬來西亞官僚系統(tǒng)中馬來人的數(shù)量占80%(但獨(dú)立時(shí)馬來人的人口比例還不到50%),接受馬來語作為官方教育語言,接受馬來學(xué)校中馬來人多占名額,接受華人辦的企業(yè),必須由馬來人參與,且給予股份。
作為回報(bào),馬來政府承認(rèn)華夏人和印度人作為馬來西亞公民的一分子,同時(shí)掌權(quán)的馬來人還致力于培養(yǎng)一種新型馬來公民:他們忠誠于國家,而不是任何民族、宗教和社區(qū);把馬來官、華夏商、印度農(nóng)打造成一個(gè)有高度認(rèn)同感的混血馬來人。
不過,這種對(duì)華夏人、印度人的公開歧視,產(chǎn)生了非常嚴(yán)重的后果,是導(dǎo)致馬來西亞工業(yè)化功敗垂成的一個(gè)關(guān)鍵因素,這個(gè)我們后面的章節(jié)會(huì)專門論述。
烙印:出口型經(jīng)濟(jì)的重新起航
由于在1957-1969年,馬來政府重心在華夏、印度和馬來人的經(jīng)濟(jì)權(quán)力博弈,經(jīng)濟(jì)成就一直不溫不火。
1970年,馬來西亞仍然是一個(gè)標(biāo)準(zhǔn)的農(nóng)業(yè)國:制造業(yè)產(chǎn)值占GDP比例不到13%,在當(dāng)年出口的5種主要商品中,仍然以橡膠、錫、木材、椰子等農(nóng)產(chǎn)品、工業(yè)原料為主,占據(jù)了出口額的78.4%。
盡管如此,這也是英國留下的寶貴遺產(chǎn),英國通過殖民時(shí)代的運(yùn)營(yíng),為馬來西亞奠基了錫礦、橡膠等初級(jí)加工業(yè)的基礎(chǔ),并通過建造鐵路、港口和城市,打通了全國的經(jīng)濟(jì)網(wǎng)絡(luò),更可貴的是,開拓好了橡膠、錫、木材以及石油在歐美的市場(chǎng)。
《馬來西亞史》評(píng)論說:馬來西亞繼承了一種東南亞國家都羨慕的出口型經(jīng)濟(jì),在馬來西亞獨(dú)立后,獨(dú)立政府同意延續(xù)這種經(jīng)濟(jì)結(jié)構(gòu)。
這也是無奈之舉,馬來政府曾經(jīng)在1958年雄心勃勃發(fā)布了‘先導(dǎo)工業(yè)法令’,意圖實(shí)現(xiàn)進(jìn)口替代型工業(yè)化,但由于馬來國內(nèi)市場(chǎng)狹小,本地工業(yè),特別是重化工業(yè)無法靠自己完成資本積累,反而影響了對(duì)出口型產(chǎn)業(yè)的資本投入,最后不得不放棄。
當(dāng)然了,馬來無法實(shí)施重資金、回報(bào)周期慢的重化工體系,也和馬來三族鼎力,數(shù)目不菲的蘇丹、邦國守舊貴族相互爭(zhēng)奪利益,無法形成合力有關(guān),這里需要再次明確,馬來西亞是一個(gè)聯(lián)邦國家,各州具有較大的獨(dú)立性,還有數(shù)不清的、擁有特權(quán)的小邦主。
馬來西亞幾乎沒有進(jìn)行的土地改革,也阻礙了他進(jìn)行工業(yè)化,特別是重工業(yè)化。
悖論:大與小,騎墻與一邊倒的地緣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
馬來西亞等亞洲四小虎無法靠自身完成基礎(chǔ)工業(yè)化,特別是重工業(yè)化,涉及到地緣經(jīng)濟(jì)這樣一門顯學(xué)。
大有大的難處,落后的大國無法依靠一兩個(gè)分工產(chǎn)業(yè)(提供的工作崗位有限),像小國一樣,在人均財(cái)富方面實(shí)現(xiàn)短時(shí)間提升,但大也有大的好處,大國可以依靠龐大的市場(chǎng)和人口,自行積累原始資本,進(jìn)行重化工和基礎(chǔ)工業(yè)化,雖然慢,但一旦到達(dá)突破點(diǎn),不僅人均財(cái)富可以完爆小國家,更可以在科技、工業(yè)上達(dá)到NO.1的位置,甚至引領(lǐng)下一次工業(yè)革命,這些對(duì)于后發(fā)小國來說,望塵莫及,大國是不鳴則已,一鳴驚人。
當(dāng)然,后發(fā)小國也未必沒機(jī)會(huì)在部分工業(yè)領(lǐng)域的實(shí)現(xiàn)全球領(lǐng)先,實(shí)現(xiàn)人均財(cái)富上的全球頂尖,但實(shí)現(xiàn)這個(gè),除了有大意志,還要有地緣經(jīng)濟(jì)的大智慧。
這個(gè)大智慧是什么,就是政治上的一邊倒,甘當(dāng)全球超級(jí)大國的鷹犬,成為超級(jí)大國在某區(qū)域霸權(quán)的利益代言人,這樣在超級(jí)大國產(chǎn)業(yè)升級(jí)后,才愿意轉(zhuǎn)移給你中等技術(shù),支援給你自身無法積累的寶貴工業(yè)資本。
日本初期背靠英國(對(duì)抗大清和俄羅斯)、后期背靠美國(對(duì)抗蘇聯(lián)和華夏),實(shí)現(xiàn)了百年崛起。
韓國也依靠處在對(duì)抗蘇聯(lián)和朝鮮的第一線,獲得了美國巨額的資本和技術(shù)轉(zhuǎn)移,實(shí)現(xiàn)了工業(yè)化。
這個(gè)支援力度有多大,給你舉個(gè)例子:
1945-1961年,美國對(duì)韓國的無償援助(包括工業(yè)品、資本和技術(shù)等)高達(dá)31億美元,不包括貸款;什么概念?1950年蘇聯(lián)對(duì)新中國,只援助3億美元,還只是無息貸款。
韓國李承晚和樸正熙政權(quán),用這些無償美援和歐洲、日本的資本,在1970年前就建立了發(fā)達(dá)的出口型輕工業(yè)。
進(jìn)入1970年代后半葉,美國和日本由于掌握了更先進(jìn)的科技產(chǎn)業(yè)(半導(dǎo)體、IT信息、通信等),便將一部分重化工業(yè),包括鋼鐵、化工、船舶、汽車以及中等技術(shù)轉(zhuǎn)移給韓國、灣灣等同盟國,韓國得以建立部分重化工業(yè),成為韓國成功工業(yè)化和進(jìn)入發(fā)達(dá)國家的關(guān)鍵密碼。
但馬來西亞既不是共產(chǎn)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(yíng)對(duì)抗的前線,也沒有和美國建立好到盟友的關(guān)系(大馬選擇了騎墻戰(zhàn)略),更遠(yuǎn)離當(dāng)時(shí)的全球主要市場(chǎng)(歐洲和北美)的輻射圈,唯一的馬六甲航運(yùn)優(yōu)勢(shì)也被新加坡?lián)屓チ恕?/p>
新加坡被驅(qū)除出大馬聯(lián)邦,是由于馬來人擔(dān)心加上新加坡,華夏人在大馬總?cè)丝诘膬?yōu)勢(shì)超過了一半,這影響馬來主導(dǎo)大馬聯(lián)邦的戰(zhàn)略,但也因此失去了馬六甲航運(yùn)的地緣經(jīng)濟(jì)利益。
可以說,馬來西亞在20世紀(jì)后半葉,客觀原因加上大馬政府的決策,凸顯它們的地緣經(jīng)濟(jì)優(yōu)勢(shì)不明顯。
借力:跨國資本送我讓青云
不過幸運(yùn)的是,進(jìn)入1970年代中后期,日本在得到高等技術(shù),韓國、灣灣等這些美利堅(jiān)盟友在得到部分重化工業(yè)以及中等技術(shù)轉(zhuǎn)移后,便把勞動(dòng)密集型的組裝輕工業(yè)轉(zhuǎn)移到了馬來西亞、泰國等亞洲四小虎地區(qū),這給馬來西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(jī)遇。
借著跨國資本帶來的組裝工廠、資本、低等技術(shù)以及歐美市場(chǎng),馬來西亞開始布局自己的(組裝)輕工業(yè)。
當(dāng)時(shí)的大馬總理馬哈蒂爾·穆罕默德提出“向東看”政策,敞開胸懷迎接全球的勞動(dòng)密集型產(chǎn)業(yè)轉(zhuǎn)移,特別是來自日本的,于是三菱、夏普、豐田以及耐克、三星、大眾等跨國資本紛紛在馬來西亞西海岸建立代工廠、組裝廠。
一時(shí),馬來西亞的經(jīng)濟(jì)好風(fēng)憑借力,增速上青云:并在1988-1996年達(dá)到了巔峰,年均增長(zhǎng)8.47%,與當(dāng)時(shí)的中國、韓國爭(zhēng)先;人均GDP在1996年達(dá)到了4798億美元,是泰國的1.6倍、印尼的4.2倍,越南的16倍,在東南亞大國中首屈一指。
在大好的形勢(shì)下,馬來西亞迅速從農(nóng)業(yè)國向(輕)工業(yè)國轉(zhuǎn)型:
1990年,大馬制造業(yè)產(chǎn)值占GDP達(dá)到了44%,一個(gè)極高的水平,農(nóng)業(yè)產(chǎn)值占比則從1970年的31%,降到19%。
在以雪蘭、馬六甲州為主的工業(yè)區(qū),馬來西亞建立了自己的汽車工廠、電器廠、機(jī)械廠,椰子叢林中的大馬都市,一派欣欣向榮之象。
野望:第一世界工業(yè)國的愿景
在大馬激情沖刺的1991年,總理馬哈蒂爾雄心萬丈的提出了:馬來西亞2020愿景,即:在2020年,大馬GDP增長(zhǎng)8-16倍,達(dá)到和發(fā)達(dá)國家一樣的工業(yè)水平,讓馬來西亞重獲第一世界的地位,如同歷史上三佛齊和馬六甲王朝,平衡于東方和西方,歐美和東亞,得到世人的尊崇。
為了完成發(fā)達(dá)工業(yè)國家的野望,馬哈蒂爾認(rèn)為馬來西亞不能僅僅依靠出口型組裝輕工業(yè),必須產(chǎn)業(yè)升級(jí),配套提出了“多媒體超級(jí)走廊”,試圖探索出一條發(fā)展信息通訊和高科技產(chǎn)業(yè)的進(jìn)取之路,“多媒體超級(jí)走廊”戰(zhàn)略核心是:讓大馬成為“世界芯片生產(chǎn)中心”。
無奈:從衣服縫紉到半導(dǎo)體封裝的產(chǎn)業(yè)升級(jí)
但實(shí)事求是的講,信息通訊和高科技產(chǎn)業(yè)作為歐美日韓的核心競(jìng)爭(zhēng)力,是斷然不會(huì)轉(zhuǎn)移給外圍國家的,甚至他們內(nèi)部還在爭(zhēng)奪。
1985年后,由于日本半導(dǎo)體領(lǐng)域和美國競(jìng)爭(zhēng)激烈,半導(dǎo)體儲(chǔ)存器全球市場(chǎng)占有率一度高達(dá)50%,這惹怒了美國,通過對(duì)進(jìn)入美國市場(chǎng)的日本半導(dǎo)體儲(chǔ)存器征收100%的反傾銷稅,對(duì)韓國三星只征收0.74%的反傾銷稅,把日本半導(dǎo)體儲(chǔ)存器打的推出了全球市場(chǎng),韓國三星則趁勢(shì)崛起。
法國電信巨頭阿爾卡特被美國司法制裁,也是我們?cè)斨墓适隆?/p>
歐美日韓聯(lián)盟內(nèi)部尚且打得頭破血流,大馬恐怕湯都沒得喝,而靠自己發(fā)展,又回到了馬來西亞發(fā)展基礎(chǔ)工業(yè)、重化工業(yè)的難題:一是國內(nèi)市場(chǎng)狹窄,無法積累的起研發(fā)高科技產(chǎn)業(yè)需要的巨額資本,另一個(gè)則是馬來自身專業(yè)人才的嚴(yán)重欠缺。
大馬想要發(fā)展信息通訊和高科技產(chǎn)業(yè),但馬來西亞的大學(xué)不能夠提供足夠的理工科技術(shù)人才,缺口嚴(yán)重;更糟糕的是,在嚴(yán)重欠缺高技術(shù)人才的狀況下,馬來西亞的高技術(shù)人才竟然還在外流。
正如我們上文所述,大馬政府對(duì)華夏人、印度人的“教育歧視”,高等學(xué)府給他們只留下極少的名額。這讓大馬的華夏學(xué)生在初高中時(shí)期就到美國、中國臺(tái)灣、中國大陸就讀,或考取他們的大學(xué),畢業(yè)后直接留在了當(dāng)?shù)毓ぷ鳌?/p>
這個(gè)名額歧視到什么程度?在2018-2019馬來西亞大學(xué)預(yù)科班中,占人口近30%的華夏人,只得到了4.91%的名額,而馬來新文化運(yùn)動(dòng)的淺嘗輒止,導(dǎo)致大馬社會(huì)和學(xué)生,不熱衷技術(shù)崗位、技術(shù)專業(yè)。
歐美日韓不會(huì)轉(zhuǎn)移技術(shù),自身無法負(fù)擔(dān)巨額研發(fā)成本,高端人才嚴(yán)重外流,最終導(dǎo)致馬來西亞的高科技產(chǎn)業(yè)升級(jí)取得了面子上的成功。
為什么說是成功了?因?yàn)榇篑R的確成了全球前幾的電子通信產(chǎn)品以及半導(dǎo)體芯片的出口國,2017年,從大馬進(jìn)口的半導(dǎo)體芯片占中國進(jìn)口總額的20.9%。
又為什么說是面子上的,因?yàn)檫@些大馬的半導(dǎo)體芯片,都是英特爾、AMD的封裝廠出口的,大馬只是做高科技產(chǎn)品的組裝,而不是自己的技術(shù)和品牌。
從衣服、電器組裝、到半導(dǎo)體芯片封裝,逼格高了,但內(nèi)核沒變。
夢(mèng)斷:97亞洲金融風(fēng)暴的重?fù)?/h1>
大馬的產(chǎn)業(yè)升級(jí)之路換湯不換藥,同時(shí)組裝+代工的比較優(yōu)勢(shì)卻在慢慢消失,因?yàn)闁|亞華夏國的比較優(yōu)勢(shì)正在崛起,跨國資本逐利而遷移,而一場(chǎng)金融風(fēng)暴,更給突飛猛進(jìn)的馬來西亞劃上了休止符。
由于不掌握核心技術(shù),國內(nèi)資本過于弱小,馬來西亞的出口型輕工業(yè)高度依賴外資,國內(nèi)高消費(fèi)又上來了,進(jìn)口增多,馬來西亞出口創(chuàng)造的美元量逐漸不能支撐進(jìn)口所需的美元,在大馬貨幣吉特和美元的供需上,美元是供不應(yīng)求,這就給華爾街金融資本提供了狙擊良機(jī)。
索羅斯一番騷操作,亞洲小虎紛紛中槍,股價(jià)暴跌、貨幣貶值,雖然馬哈蒂爾拒絕大馬國貨幣大幅貶值,拒絕IMF的援助(趁機(jī)抄底優(yōu)良資產(chǎn)),并對(duì)國內(nèi)資本管制,大體穩(wěn)住了態(tài)勢(shì),沒有像泰國一樣,被西方資本吃了個(gè)精光,但大馬也因此讓西方資本不滿,大馬的高速增長(zhǎng)時(shí)代結(jié)束了。
大馬想要重歸第一世界工業(yè)國的夢(mèng),也醒了。
此后,馬來西亞、泰國、墨西哥、智利等靠出口型輕工業(yè)崛起的國家,紛紛陷入低增長(zhǎng)和中等收入陷阱的怪圈,被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家研究至今。
盡管,西方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家診斷出了不民主、政府腐敗、人種不勤勞、文化沒有技術(shù)基因等種種病癥,但對(duì)于馬來西亞這樣的后發(fā)國家來說,它的第一世界工業(yè)國夢(mèng)斷沉沙,主要還是以下幾個(gè)原因。
1. 國內(nèi)市場(chǎng)狹小,無法靠完成基礎(chǔ)工業(yè)化、重化工業(yè),也無法承擔(dān)得起向高科技轉(zhuǎn)型的巨額研發(fā)成本。
2. 處于地緣經(jīng)濟(jì)圈的外圍,既不是歐美日韓同盟圈的小伙伴,無法得到先發(fā)工業(yè)國的資本援助和中高技術(shù)轉(zhuǎn)移,也不靠近主要需求大市場(chǎng),靠距離優(yōu)勢(shì),獲得產(chǎn)業(yè)鏈的輻射。
1980年,馬來西亞人均GDP為1774美元,比韓國的1704美元還高,但隨后,韓國靠著部分美日轉(zhuǎn)移的重化工業(yè)以及高科技業(yè),將馬來遠(yuǎn)遠(yuǎn)甩在的后邊,到2018年,人均已是馬來西亞的三倍。
3. 馬來西亞的馬來人至上政治,導(dǎo)致華夏人、印度人等人才不得其用,大量流失;穆斯林新文化運(yùn)動(dòng)的淺嘗輒止,導(dǎo)致馬來人沒有對(duì)技術(shù)、生產(chǎn)力的渴求;而靠著老天爺賞賜的錫礦、石油,靠著豐富的橡膠、椰子,也可以活的很舒服,心氣弱了,馬來西亞在工業(yè)化能夠到達(dá)的上限,被大大消弱了。
好了如果你需要快速辦理馬來西亞工作簽證也可以找小曹,同時(shí)小曹目前也在專賣馬來西亞燕窩,如果您有相關(guān)需求可以通過樓下燕窩鋪商城在線購買燕窩。
贊賞 微信贊賞
微信贊賞 支付寶贊賞
支付寶贊賞